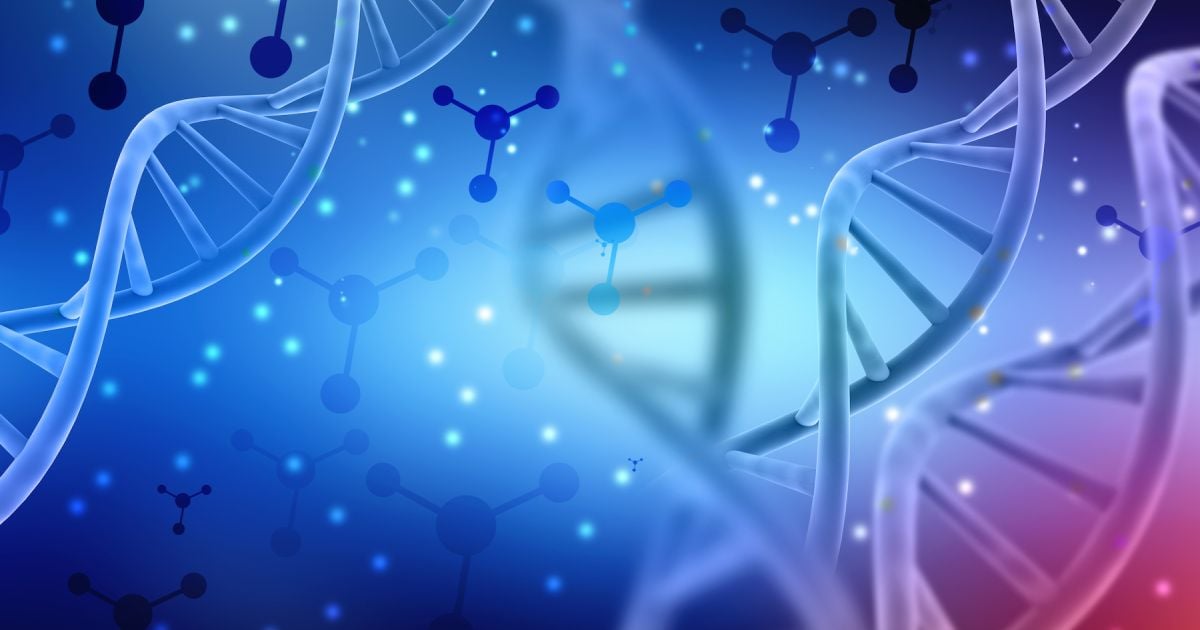
本文转载于微信公众号“深蓝观”,原创李昀,文中“陆羽”为“Jason koo”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j_yCKF5169uub6ZBXpQwg
整个2022年,资本对biotech产业的态度起起落落:对于融资到三四轮的企业,观望不前,等待它们估值下跌;对于更早期项目,资本却保留了最后一丝慷慨。
根据医药观澜统计,整个2022年,至少有270多家中国创新药公司宣布完成了超300起不同轮次和性质的融资,其中早期融资(B轮以前)案例占到了总数的约65%。于近三年内成立的公司占到了约43%。
一些初创的单轮融资一度让人回想到了biotech的全盛时代。比如,专注于开发治疗衰老相关退行性疾病新药的维泰瑞隆、专注于生物技术药物及创新小分子药物研发的科伦博泰甚至完成了2亿美元的B轮融资。
而另一方面,这些刚刚学会走路的biotech初创,依旧无法得到市场的信任。2022年,A股IPO的50家医药生物企业,有19家破发,占比近4成。亚虹、迈威、益方……这些只有在研管线做支票、还没收获商业化第一桶金的biotech初创,在资本寒冬下只能踉跄亮相。
两年以来,资本开始对biotech逐渐失去耐心,而这些初创企业还没来得及自我证明,就被迫要先自我调整。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便是管理人才团队的换血。2015年后,随着创新药创业大潮的涌进,管理团队的聘用有一套可以复制的模板:藤校毕业、博士打底、跨国药企经验,各种光环的叠加曾经为这个行业吸引来了无数钞票和无数希望。
然而,和大众对创新药产业逐渐冷静回落的认知一样:如今biotech创业对于人才的需求,也进入了一个讲求实际的时代。
首先,大药企带管线的资历,不再是一张万能通行证。
“以前这些biotech创始人,从原来大厂出来时都已经五十多岁了。biotech公司的成长期少说十年,那时候他们都六十多了,还能剩下多少冲劲和理想主义?”从事biotech行业猎头工作的陆羽(化名)分析道。
因为工作原因,陆羽曾经和很多biotech创始团队有过接触。在他的经验里,这种年纪偏大、经验丰富的创始人经常会掉入一种思维惯性或惰性之中:手里有管线,资本有钱,通讯录里有熟人,就立刻搭台干活。但是不管是眼光还是资源,这种撺局式创业都没有保鲜的动力和足够的能力,最后都掀不起太大的浪花。
其次,原来在biotech行业吃香的海外背景如今也不必然加分。
中美经贸的偶发摩擦,和biotech逐渐被举国体制收揽、被集采前景导往转型的大背景,让外籍高管逐渐失宠,也让曾经带动过中国创新药产业的海外回流人才无法再发挥出那么大的作用。
“体制内”成为了biotech创始团队招募的最新热门标签。“现在国家鼓励产教研结合,市场和政策都鼓励一些体制内的教授专家出来创业,地方政府也给了特别多的支持。现在VC就特别看好这一批人,因为他们的体制内身份可以保证比较稳定的社会资源和科研产出。”陆羽说。
最后,创始团队的形象,不能再以单纯的科学家自居了。过去一年的医药二级市场,板块轮动的速度可以用疯狂来形容;而在创新药板块,几年前还人钱拥挤的单双抗技术早已不能博得资本的惊喜一笑。诸多迹象表明:市场在系统性危机前已经逐渐失去稳定的投资方向。
这时,一个合格的biotech创始人只专精科研远远不够,还要能够在混乱嘈杂的环境中做决策、拿主意、稳阵脚。“有些创始人在我们老猎头来看,可能也就是D级别。他只是在自己专注的那一块领域比较厉害,这种人要在初创公司里做到总监级别以上,必须学习能力特别强,得了解整个大市场的动态,也得经营和其他团队成员、和投资机构之间的关系。”陆羽说。
无论biotech的投资者们如何叫苦,行业的朝阳属性依然无法否认。而对于这一片朝阳中最年轻的企业而言,“年轻”的标签是资本,也是压力。成长对于他们而言,也许正意味着从实验室走向生意场、从简单走向复杂的阵痛。
当互联网遭遇创新药
Biotech的行业氛围,从来都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象牙塔。尤其是它最热的时候,来自四面八方的钱也带来了五花八门的风气和文化。
2015年百济、和记黄埔纳斯达克上市,biotech概念在中国大火,一群房地产老板率先拿着热钱进入生命科技领域,做矿业、百货的随即跟上,什么技术最火投什么,于是造成了PD-1、CAR-T资源过剩的历史遗留问题;
而202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流量瓶颈期的到来,以BAT为代表的大厂们纷纷掷金biotech,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四年时间,百度风投共参与41起医疗硬科技拟投资,数量还在逐年上升,其中的成果代表是做AI药物发现的百图生科。阿里巴巴旗下的云峰基金投资了两家新药研发公司,腾讯已经接连投资多家创新药企,去年新持股的丹序生物创始人,还被网络包装成了“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
在陆羽的观察中,创新药行业对于互联网的介入并不买账。“他们会觉得这些互联网人特别low,觉得他们不懂科学,只会砸钱和营销。”而之所以最后还是选择开门迎客,背后其实有两层原因。
其一是AI制药意外成为了联通两个世界的接口。
这股技术潮流率先引爆美股。Biotech行业有一个魔咒:每过十年,药物研发的成本就会翻倍。根据德勤报告,2010年TOP12生物制药企业的研发汇报率在10%左右;而到了2019年,这个数字骤降到可怜的1.8%。
于是乎,AI药物研发平台应时而生,被看成了biotech的成本救生圈。2020年,薛定谔和Relay Therapeutics打响AI制药上市第一枪。前者市值一度超过80亿美金。
受美国市场影响,2020年国内AI制药行业融资额超过27.23亿元,比前一年上涨了十倍。这也成为互联网资本名正言顺进击biotech的抓手:除了钱以外,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方面的技术积累,给了BAT们投注的底气。
其二是biotech初创企业这些年逐渐从重资产转向轻资产。已经成型的龙头们尚且断臂求生;对于创业公司而言,在资金紧张的压力下,精简业务部门、和合作伙伴共担风险便成为了自然选择。
比如biotech初创企业腾盛博药,就把新药的临床优化和上市普及,交给了更懂数字化平台的阿里健康来做。合作的背后必然有资本的连带: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的股东博裕资本,以及马云持有的云锋基金,都在腾盛博药有不少的持股。
Biotech初创企业拿了互联网的钱、承认了互联网的合作角色,也就意味着必须接纳互联网行业的影响输出。而这也造成了很多传统制药行业出身人才的不适应感。
大多数Biotech公司的核心是一个个高度专注的科学家团队,因此形成了许多专业知识的的孤岛。互联网更像是一条迎来送往的货船,把来自资本和市场的外界信息携带进来:打破了孤岛的封闭,也打破了孤岛的宁静。
“互联网公司的思维就是要快速迭代,而这些制药公司出来的人特别不能理解这种996的紧张感,觉得做科学不能这样急功近利。互联网公司想要很快地做一个产品出来,但这些药企思维的员工就觉得做科研不能像打仗一样,而是需要时间和技术的逐步累积。”陆羽说。
两种文化的撞击,给了初创biotech不小的管理难度:一面是金主和金主派来的人,另一面是干活的科学家,两面都得罪不起。陆羽以百图生科举例:创始人想要把两种文化里的人拧成一股绳,但究竟谁来做决策方,谁来做工具方,最后也没有协调明白。
如今,资本对AI的热情已经不复当年,AI技术在制药方面的技术成果有限,也不可能短期内改变整个行业。但这一段经历让biotech初创企业明白:未来的人才管理,不再只能依赖一条路走到底的科研思维,而是要面临各种资本和技术的交叉路口。
熟人陷阱:老团队和新变化
Biotech初创企业,天生就带着新与旧的矛盾感。
药物研发领域因为门槛高,人才流通有限,跳来跳去就是那么几张熟面孔;而市场期待着产业破旧立新,用老人做不出新东西。
更何况,初创企业在资本面前人微言轻,灵活性是生存下去的关键。今年资本市场看好双抗,明年转头就倒向ADC,市场的心思多变难测,作为一家初创企业,要有随时调整团队组合的速度和魄力。
而在陆羽看来,如今支配着biotech初创企业人才招聘的,依旧是人情。这也让很多企业落入了熟人陷阱。
“很多创始人找来的管理人才,都是以前的老同事或者老部下。这些人大多数不太有领导能力,也一直抱守着传统药企的那些规则。他们在市场认知上比较落后,但是碍于情面,也不太可能被换掉,就一直占着这个位置。这就导致企业的发展很缓慢,因为年轻人、更有能力的人进不来。” 陆羽说。
尤其是这两年,90后占据了投资圈的大半江山。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听一群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聊前瞻,代沟不仅存在于对技术迭代的认知上,还有整个世界观:对价值的理解、对风险的接受、对变化的喜恶。
Biotech在这两年也经历了生物行业车轮战的洗礼,资本的进场和撤退让这些行业老兵们意识到:并不存在吃遍天的一招鲜。曾经高调的AI制药在去年开始退潮,一整个2022年,只有剂泰医药一家公司趟过了1.5亿美元的融资基线。盈利模式尚未走通,裁员风波已经来临:上市仅仅一年的AbSci,裁员人数约占20%,股价已下跌85%。
反倒是CRO 这样小步前进的领域,满足了这段时间保守的资本心态,从而迎来了继2016、17年融资潮后的第二春。普瑞盛、百英生物、昆翎、科莫医药等CRO企业都在去年取得了不错的融资成绩。
相较而言,大药企更适合科学家思维。从学术角度来说,激进永远正确:研发热点不会消失,一种药物技术的成熟可能需要半个世纪,大药企有足够的体量支撑这五十年的试错。而biotech初创,却时不时地要向市场的保守低头:别说五十年,一年的时间就足以让一家公司从宠儿变成尸体。
对于能量孱弱的biotech初创,市场存在着太多的“灰天鹅”事件:它们虽然不会像“黑天鹅”那样一击毙命,却足以在短时间内打乱公司自然发育的节奏。比如这两年的新冠疫情,疫苗和口服药市场被捧上C位,不少本来没有相关管线的biotech初创,在资本的催促下也不得不延伸触角。
如今已经初露锋芒的和铂医药,在新冠大流行前还只是一个成立了三年的小朋友。本来公司做的是肿瘤免疫类药物,但在疫情期间仍是不能免俗地做了新冠抗体ABBV-47D11。只不过,和铂在满足市场期待后懂得及时抽身,将开发权益做了一次性转让,让整个公司的主线一直保持在笔直的轨道上。
一些biotech初创就没有和铂这么幸运了。陆羽说,很多高管带着自己领域的技术、经验和资源加入公司,结果老板迫于市场口味的压力而要求自己换线。在这种情况下,人事摩擦在所难免。
“之前我接触过一家biotech初创。当时招了一名背景特别好的科学家,创始人和投资人都觉得稳了。但后来发现他对新引进管线的适应力根本不行。这些初创企业除了自研管线以外,还得有应投资人建议‘加塞’的其他管线,这就要考研管理者的商业和人际协调能力。”陆羽说。
对于这一类科学家型biotech高管而言,从研究生、博士、再到研究员、管线领头人,一个药物领域做了十几年,要想跳脱自己的专精方向是很困难的。而在biotech初创卖管线越来越频繁的现在,等待他们的结局往往就是:茶凉,人走。
“真正的出海,是五湖四海的钱都要拿”
biotech初创团队之所以看重海外背景,无非是想要招到吸收了发达国家医药产教成果、有利于出海转化的人才。
但在陆羽看来,真正的出海除了做成几单license-out,或者把药卖进海外市场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具备一种无问东西的拿钱能力。
“很多biotech创始人都在中美之间非常徘徊,”陆羽根据他多年来的观察总结,“他们总是在想:到底是要做成个美国企业还是中国企业?一方面,华人科学家在美国是很难融资的;另一方面,中国的产业政策又比较特殊,创业风险是比较大的。”
这种徘徊体现在biotech上市前在A股和美股之间的举棋不定上,也体现在这些企业临床中心和研发中心的全球布局上。但中国还是美国、国内还是海外的选择题,事实上是一种对自身吸引力不够自信的受限思维。
这些年来中国Biotech的步伐,一直在跟着市场友好度走。不论是十年前生物科技领涨美股,还是后来的中概股、科创板,这些奔着IPO的企业一直致力于找到一个相对宽松的容身之所。但政策的松紧、市场资金池的大小一向飘忽,导致biotech的后续发展还要看人脸色。
在陆羽看来,要想改变biotech被牵着鼻子的处境,企业必须转变思维:委身一个好拿钱的环境,不如建立一种主动找钱的能力。
biotech初创企业Insilico Medicine就是一个反例。这家去年刚完成了D轮融资的企业,投资朋友圈的组合极为丰富:有传统大资本礼来,也有行业内资本药明康德;有韩国未来资产集团,也有波士顿投资集团。
曾经,Insilico来中国融资成为明星标的,最近又频繁出现在中东国家的行业场合。去年公司收获的950万美元融资,领投方正是沙特石油公司旗下的风投基金。
而这样一家成分多元的biotech,其实是一家创立在巴尔的摩市的美国公司。
Insilico能够在美国投融环境紧缩的当下,打开机会局面;由此看来,年轻、没钱、疫情、经济下行都不是中国biotech初创们偏居一隅的理由。
“要论专业背景,Insilico的创始人Alex可能真的比不上我接触过的中国biotech创始人。但他懂得怎么包装自己和团队,创业做成了网红,每天都在互联网上向公众输出观念。在这一点上,中国biotech初创团队做得差很多,大家总觉得这个行业是拿实力说话的,不用拿故事说话。”陆羽说。
“biotech就是一个贩卖希望的行业。中国的biotech创始团队必须理解这一点,才能卸下包袱,意识到公司的marketing和个人的branding的重要性。”陆羽补充道。
biotech初创需要认识到:再高新科技的行业,本身也是个生意。而只有当初创人才们真正以生意人的身份自处的那一天,之前对许多标签的执着和迷信才能被打破,企业才能走向这个世界的更多角落。

